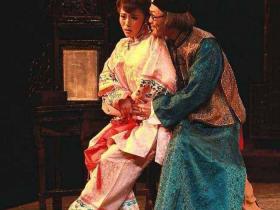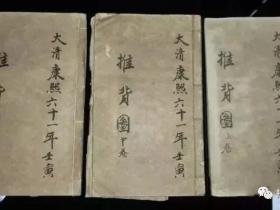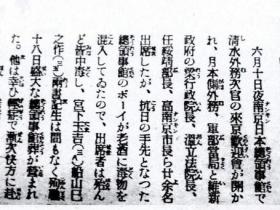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过去70多年了。
每当我们纪念胜利的时候,总是不会忘记那些凝结着千百万人生命和鲜血的经典战役,不会忘记那些前赴后继冲锋陷阵的战士和人民,也不会忘记青纱帐里的梭镖大刀、俄罗斯夜晚的“喀秋莎”、诺曼底登陆的冲锋舟、太平洋上的舰队和机群,但是,却很少有人了解这样两个观点:“对于美国的许多战士而言,图书是他们最重要的武器”;“苏联文学中的军人形象及其所反映的战争问题,增加了我们的斗争力量”。
在此,我想就上个世纪40年代前后中美两军战时阅读情况做一个比较分析。
“带着图书上战场”
——美军的阅读及图书供给
早在1940年下半年,美军就开始制订了一个为所有训练营地订购图书的庞大计划,其具体目标细化分解到每一个新征入伍的士兵。但结果是编制5000人以上的部队才能获得此项经费,而少于1000人的部队则得不到资金支持。经媒体披露这一情况后,由美图书馆协会倡议并经政府批准,在全国发起了一场向军队捐赠书籍的“国防图书活动”。随着美军参战进程,不久活动正式更名为“胜利图书运动”。
到1943年上半年,其已为军队募集到900多万册图书,当送达前线的时候,图书成为了广大官兵最重要的武器,他们“在图书中找到他们需要的力量,减轻了身体在战场上受到的伤痛,获得治愈情感和心理伤疤的力量”。同时捐赠活动还成功地把全国人民团结于共同的荣誉感中,“在战场上的战争获得胜利前,他们已经提前在精神上获得了胜利”。
由于赠书数量和质量都受到一定局限,无法满足前线士兵的阅读需求,历时两年多的图书捐赠活动于1943年10月画上了句号。但为前线输送图书一天也没有停止,一个更大胆且富创意的“军供版图书”计划由此展开了。这段时间被《时代周刊》称为“美国150年出版史上最值得注意的时期”。
为确保这项专为美军量身订制的图书计划有效实施,出版部门专门研究了士兵制服的口袋尺寸,做到大号的“军供版图书”能够装入士兵的裤袋,小号图书还能够装入士兵胸前的衣袋,而较小的图书实际只有钱夹那样大小,让前线士兵能迅速塞到口袋里。对图书内容则注重多样化,凡受士兵欢迎的当代小说、历史小说、神秘小说、幽默故事以及西部小说,还包括励志、冒险、航海、历史、传记、游记、漫画、古典文学、音乐、诗歌、科学等,都在出版选择范围,以适应广大士兵的阅读趣味。
可以说,“军供版图书”为精疲力竭、命悬一线的战士提供了有力的精神依托,在他们为突破德军长达6000公里的坚固防线做准备时,已把“军供版图书”作为重要的武器随身携带,给了他们超常的胆量、勇气和魄力。整个战争期间,美国为前线军人免费提供了超过1.2亿册图书,在美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书店要随军行动”
——我军的阅读及图书供给
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中国工农红军处于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的双重“围剿”之中,由我党领导的中国左翼文艺战线以笔为枪,全力支持红军救亡图存的斗争。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创作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毁灭》,曹靖华翻译绥拉菲莫维奇创作的“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的成功之作《铁流》,还有夏衍翻译的高尔基名著《母亲》等等,被送到根据地和红军部队,成为当时部队官兵极其难得的宝贵读物,对于引导青年投身革命、坚定信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红军到达延安后,党中央决定正式成立新华书店并逐步向陕甘宁以外地区拓展。随着八路军东进抗战前线,一二○师在所属三五八旅随军文化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了晋绥新华书店,这不仅是新华书店在延安以外地区建立的第一家分店,也是我军书刊发行网络的一个关键节点,成为向各大抗日根据地发行的重要枢纽,凡从延安运来的书刊都要先集中到这里,然后再发送到晋察冀、太行山、冀鲁豫等敌后抗日的部队。
接下来成立了晋察冀书店、华北书店、关中书店和冀鲁豫书店,在日本鬼子疯狂扫荡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用当地生产糊窗户的土纸,釆取石印的方式,首先出版了列宁的《论左派右稚病》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两本书,后又用木刻字模翻成铅字,再后来到敌占区买来铸字炉与字模,出书品种逐渐增多,除政治军事类书籍,还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文艺书,在前线部队引起很大反响。在新四军皖南根据地,由新知书店武汉总店在云岭开办了一个抗敌书店,后改名战地书店,再后来,屯溪的生活书店分店也迁来云岭,两店合并统称“随军书店”,成为我军在抗日前线部队开设的第一个“随军书店”。
“随军书店”里不仅有专为部队编印的《抗日战士读本》,还有大批适合基层官兵阅读的通俗读物、革命理论和文艺书籍。云岭的随军书店还组织了两个图书流动供应队,分赴苏皖两省的长江南岸地区售书,后来还组织力量,把图书运到长江北岸的新四军指挥部和第四支队的驻地去。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领导指示“书店要随军行动”“要充分做准备,待我军打出去时到新解放区开展书店工作”。到1947年4月,山东新华书店即华东新华书店在华东野战军建立了“随军分店”,下辖5个中心支店、24个支店和21个小型图书馆,在部队统称“随军书店”。在两年多时间里,共计发行图书50万册、印行图书24万册,在淮海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11月,军委总政治部和中宣部联合向全党全军转发第三野战军的做法,决定在各野战军与军区部队建立“随军书店”,兵团及军设中心支店及支店,工作内容以图书阅览为重点,图书种类兼顾官兵各自特点。
随后,军委总政治部又作出部署,把已经建立的“随军书店”向师团延伸拓展,还要有计划地到连队举行巡回展览和借阅,让图书走进基层,成为战士的良师益友。
探索网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统帅部统抓统管
——两军图书工作的共同特点
中美两国都是由进步的社会文化团体率先发起,给自己的军队捐赠图书,美国是图书馆协会和战时图书协会,中国是左翼文联和中苏友好协会;接着得到两军统帅部的首肯和支持,从美军情况来看,罗斯福总统当众向士兵赠送图书,高度评价胜利图书运动以及其他组织图书的活动,并且发表声明“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知道,图书便是武器”。
在美国劳军联合组织的支持下,经美军特殊服务部的具体组织协调,在纽约建立一个大型的组装仓库,专门接收来自各地的数千万册书刊,经过分类装订成套发往前线。
诺曼底登陆前夕,美军准备了近100万册图书专门发放给即将登船的部队,而且做到人手一册。一本书仅几盎司的重量,“军供版图书”成了军人可携带的重量最轻的武器。在发起行动那天晚些时候,登陆的士兵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身受重伤的战友靠在悬崖边读书的场景。
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士兵登陆塞班岛的四天内,海军就迎来了一艘满载图书的船只。当“军供版图书”到达的时候,他们会如饥似渴地抢到一本,收藏起来,带着参加战斗。
从我军情况来看,毛泽东在延安亲笔为新华书店题写店名,还指示“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并且与中央出版发行部门的同志一起在窑洞里研究规划,向各个抗日根据地运送图书的线路,确定最近、最快、最安全的书刊运输线和运输方式,切实做到战斗打到那里,就要把图书送到那里,力求覆盖所有重要的抗日根据地。
以晋冀鲁豫军区为例,每逢大战前夕,刘伯承司令员在前线与中高级指挥员谈话时,都要求大家抓住作战间隙阅读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名著《日日夜夜》,联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向书中的主人公炮兵大尉沙布洛夫营长学习。徐向前副司令员在军区部队宣教训练会议上,专门向全体与会干部选读了《日日夜夜》中的一段,并就书中两个典型人物,即智勇双全的营长沙布洛夫和坚持狭隘经验论的团长巴甫琴科作了比较分析,生动说明现代战争中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精通战术和爱惜人力等问题的极端重要。军区政治部大量翻印《日日夜夜》运到部队,规定该书为营以上干部必读书籍之一。
进攻太原时,徐向前要求把书中描写楼房战斗的一章摘要印成战场传单,发给担任巷战的部队——因为其中以具体的形象提供了市街战斗的战术要领,对指挥员们极有参考价值。置身前线,人们就可以经常听到指战员以钦羡的口吻谈着沙布洛夫他们的名字,听到官兵们交流《日日夜夜》是怎样一本百读不厌的小说。
国情军情差异
——两军图书供给和阅读的不同做法
在美国,“军供版图书”从一问世就带着鲜明的美式印记,依赖国家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文化软实力,形成独特的政府领导下的市场化军供体制和官兵消遣娱乐的阅读取向。由战时图书协会牵头,以陆军部、海军部相关部门为主导,把经过选择的生产纸张的公司及所属工厂,负责打印排字的公司、印刷厂和各个出版商,以及图书遴选咨询委员会包括在内,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按市场规则出版发行军队需求图书的生产供应链。
从起草协议、签订合同到具体实施,既要求出版商给予较高折扣多做贡献,又适当提高图书价格确保质量上乘,满足在作战条件下长途运送、多点分发和单兵携带阅读的需要。当时的《纽约时报书评》对此作了报道:“堆成山一样的书——都是好书,包括经典著作、当前畅销书、历史、传记、科学以及诗歌——正在分发给我们驻扎在海外的部队,这是在美国图书出版商和陆军部、海军部两者之间的一种新的安排”。
最受美军士兵欢迎的书目中,《布鲁克林有棵树》和《快乐无疆》名列前茅,前者讲述阅读让卑微的生命变得高贵,知识可以改变人的修为与命运,最终依靠家庭的力量支撑孩子实现梦想的故事。后者则是从一个少女的视角讲述母亲的有趣事情,热情善良的心、滑稽的人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给战争中变得多愁善感的士兵以心理上的抚慰。同时还有《琥珀》和《奇异的果实》两本畅销书,据士兵们反映“那些最受欢迎的书至少有一个本质——包含着性爱,有时甚至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如果你看到有一本书被翻得破破烂烂了,那本书肯定就是《琥珀》。”战时图书协会执委会认为,正如美军为保卫自由而战,协会强调对军人提供不同主题的图书,甚至包括垃圾图书。
我军的做法从观念、方式和阅读都具有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本质特征,形成了当时党报舆论引导和围绕中心的思想性阅读取向。在中国抗战转入战略反攻的新形势下,中宣部和总政治部向全党全军发出学习苏联话剧《前线》剧本的通知,同时由新华广播电台向各解放区播发,各地再分别付印,成为解放区影响最大的作品。中央强调指出:“我们把《前线》全部发表,不仅因为这是苏联卫国战争中伟大的杰出作品之一,而且因为它对今天的我们也有很大的意义,为了在目前这个工作情况下我们的工作能进一步的改进,我们实有从这个剧本学到一些东西的必要。”
在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夕,我军又将描写新一代苏联红军战士在同德军浴血奋战中成长的小说《恐惧与无畏》翻译成中文大量印发,出版数量虽没有准确统计,但在每个战区总是数以万计,有的部队为适应战士的文化水平,还编写了通俗本。随后《人民日报》以《介绍一本苏联治军小说〈恐惧与无畏〉》为题,向全军官兵推荐这部反映苏联卫国战争中为祖国解放而英勇献身的战斗作品。此外,苏联作家里多夫的《丹娘》《苏联红军英雄故事》等,都是受到前线指战员欢迎的读物。
抗战胜利后,《人民日报》又刊发《要用智慧作战》的专稿,向部队推荐《恐惧与无畏》第二部,明确指出该书的主要人物营长巴武尔章,在战火中悟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战争的无情真理,不在于‘去死’这句话中,而在于‘杀敌’这句话中。”这就是《恐惧与无畏》的主题思想,它对我们前线部队的教育意义极大。党报在引导部队官兵读书时,要求首先把该书看作是一本活的“战斗条令”,然后去认识理解丰满的思想内容和活泼的艺术手法,再作为一部优秀的写实的军事小说来阅读。并且强调我们已经从“第一部”中学到了如何教育训练部队,这些方法已经在实际战斗中证实了它的力量,它的“第二部”还将帮助我们的指战员在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上不断提高。
探索网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笔像剑一样威猛”
——两军重视发挥图书在战争中特殊作用的深刻启示
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夕,我军鉴于当时没有现成合适的图书提供部队阅读,便自己动手征稿选编了30余万言的《二万五千里》,在延安的窑洞里用草纸油印成书下发全军。参加征稿选编工作的著名作家丁玲激动地说:“日夜整理着、誊清着这些出乎意外,写得美好的文章……一段一段的多么惊心动魄的场面,有声有色地被描绘了出来。”
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壮大抗日文化战线,举起文化武器以助力抗日武装斗争,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这稍晚两年的美国,战时图书协会召开了一次出版界会议,凡出席会议的专业人士都收到了以协会名义发出的《公开信》,要求作家和出版商都要思考他们在战争中的特殊角色,“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未雨绸缪,比我们的敌人想得更多,知道得更多”,“这场战争也是图书的战争……图书便是我们的武器”。虽然中美两军的表述在语言文字上略有差别,但无论是“文化武器”或“图书武器”,其精神实质都完全一致,全面战争正在进行,战争的硝烟不仅弥漫“在陆地上、海上以及天空中”,而且延伸到“思想界”。革命文化既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又是革命战线中一条必要且重要的战线。今天,我们重温七十多年前用笔与剑共同书写的那段辉煌历史,对于在新形势下建设强军文化,培养造就新一代“四有”军人,实现未来打赢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要围绕强军打赢改进军队图书出版发行工作。当前,我军面对“两个战场”,一个是烽火燃烧的战场,一个是没有硝烟的战场,给广大官兵尤其青年官兵及时提供能给他们正确引导和帮助的优秀图书,是在新形势下做好军队图书出版发行工作的紧迫任务。尽管部队早就安排了专项购置图书的经费,但从各级图书场所的现状来看、用建设强军文化的标准来衡量,仍有不小差距。
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抗战时积贫积弱的状况,我们现在的综合实力也早已远超二战时期的美军,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向部队提供数量充足、质量上乘的中国“军供版图书”。即使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与前辈们当年用木刻字模、用草纸和窗户纸油印“土八路”的“军供版图书”相比,也早是天壤之别。“两个战场”波云诡谲,瞄准打赢改革我军图书出版发行工作已是刻不容缓。
要按照军民融合发展的路子开拓社会图书资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军民融合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军民融合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过渡、进而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期。我们应该立足国情军情,借鉴美军在二战期间的历史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供版图书”路子。这既符合中央关于把军民融合发展理念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国防建设全领域全过程的总要求,又能够充分体现我们国家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坚持军队需求和国家主导相统一、社会动员和市场运作相统一,创新军队图书供给的体制机制,强化国家、军队及社会图书资源整合力度,盘活用好存量资源,优化配置增量资源,并在政策扶持、法治保障、市场流通等方面多管齐下,最大程度凝聚军民融合发展合力,实现军队图书馆室建设效益最大化。
要着眼新的时代加强对青年官兵的读书引导。现在部队官兵的阅读,既有图书质量和数量不能满足需求的问题,更有因为网络发展、手机微信和电视普及对传统读书活动冲击影响的问题,后者是比前者更突出更严重的问题,直接导致官兵阅读兴趣下降和对图书选择取向的变化。从我前几年到过的许多部队图书馆室来看,有的藏书量不算少,但真正为青年官兵喜闻乐见的却不多,那个时候就缺乏对官兵的吸引力。现在官兵上网、上微信基本能够做到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其内容的丰富多样,浏览阅读的方便快捷,时间地点可自由支配,谁还会去那个受到诸多约束限制且没有多少自己心仪图书的地方去借书读书呢?从一定意义上说,如今最难的不是书的供给问题,而是如何激发官兵的阅读兴趣。应该适应网络时代的阅读变化,做到电子书、纸质书及其他阅读形式并举,但不能用娱乐消遣代替读书,而要倡导在快乐中自觉读书。
高级军官要为基层官兵多读书读好书做表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毛泽东堪称我党我军读书楷模,曾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对我军产生重要影响的苏联战争题材优秀话剧《前线》,就是经他首先阅读后推荐介绍给全党全军的,创造了党史军史上的“三个前所未有”,党报全文刊发一个外国的话剧剧本,专门为号召全党全军阅读这个剧本发表社论,要求各部队翻印这个剧本作为整风的文件,至今党内军内仍无二例。当时八路军的三个师长林彪、刘伯承、贺龙和新四军的师长彭雪枫、张爱萍,都是部队读书好学的倡导者和带头人。美军在二战中热爱读书的风气,也与艾森豪威尔这些前线指挥官带头读书的表率作用有关,尤其大战在即,艾森豪威尔往往通过阅读小说来放松自己、缓解压力,并且要求对即将参加战斗的每个士兵配给适当数量的图书。这些做法又是与他们的开国元勋、杰出的军事统帅华盛顿酷爱读书留下的影响所分不开的。华盛顿生前阅读、保存的出版物有1200多种,大多是书,在后来美军官兵的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个驰骋疆场的赳赳武夫,还是一个终生追求知识,勤勉自学的读书人。身教重于言教。高级指挥官自身模范作用,对部属就是无声的号令,自然会让多读书读好书在军营蔚然成风。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原第二炮兵政治部副主任)
原标题:“军供版图书”与“随军书店”——中美两军二战前后阅读情况比较分析
探索网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