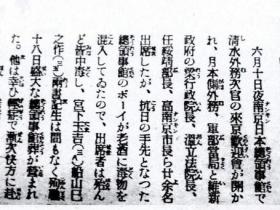■赵武平
目前所见《饥荒》文稿,系译者自存的英文打印本,但毕竟不是经过编辑的定稿,未免存在舛误,遗漏,和前后矛盾之处。也就是说,就未刊稿从事回译,要比通常的文学翻译,还要多出一个前期准备,即以文稿释读为基础的文本鉴别和厘定。唯有对英译稿进行考证、研究和完善,才有可能使随后的翻译和修正,不会因为误入歧途,留下或多或少的缺憾。
【释读】
原稿辗转保存,历经六十余载,依然大体完好,只有不多几处,微见瑕疵。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打印墨色不匀,再加岁月磨蚀,致使部分文字漫漶;二是未经编校,文稿有讹误,亦可见缺漏。因此,动手翻译之前,要进行释读和校勘,即参照一九四六年版《惶惑》和《偷生》,一九五〇年《小说》月刊连载的《饥荒》章节,以及一九五一年版哈考特版本,判别原译稿和原著的差异,同时辨认模糊字词,标记拼写异常与错误,以及语句缺失。
《饥荒》未曾全文发表,全面校勘译稿,自然无从谈起。但故事的连续性、人物的发展和情景的呼应,加上哈考特版对原著的后半部,尚有难得的保留,又能使译稿得到部分校勘,从而确定译文中明显的专有名词变化。此外,在错译鉴定和语句补阙方面,类似“理校”式的“对勘”之法,也能收到一定之效。
比如,在第二十五章,日本宪兵来巡查防空准备,责打李四爷失职,遭到反抗后兽性发作,“四双后跟带着钉子的靴子,像四辆坦克车似的,一齐向老人的两条腿踢过来”(Four pairs of boots like four tanks with nails on the heels kicked together at the old man’s legs)。单就句子本身而言,看不出什么毛病。但就上下文看,即会想到两个宪兵,不可能有“四双”靴子。因而,可以断定第一个“four”,乃“two”之误,正确的句子当是“两双后跟带着钉子的靴子,像四辆坦克车似的,一齐向老人的两条腿踢过来”。这个推断,在哈考特版第三部第十八章中,也能找到支持:编辑似应发现错误,故而改之为“宪兵的靴子凶狠的踢向老人的双腿”(The boots of the gendarmes kicked viciously at the old man’s legs)。
又如第三十四章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The children wanted to fire crackers, but could find none in all Peiping. one wipes the dust off a table. War is a serious illness of mankind. When the human race has been ill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recover?
译成中文就是:
“孩子们想放鞭炮,可是全北平,一个都找不到。擦掉桌上的灰尘。战争是人类的一场大病。人类生病了,完全康复需要多久?”
第二句明显是残句,和前后文都不衔接。原句是什么呢?
对比哈考特版,在第三部分第二十六章,能看到原稿虽经删并,仍有一句完整保留:“一个被征服的国家的悲伤与苦痛,不像是桌上的灰尘可以抹去,是不能被胜利给扫除净尽的”(The sorrow and pain of a conquered nation could not be swept away by victory as one wipes the dust off a table)。
可见,完整的原句就是这一个,找不回整句,无以补阙,更遑论全篇还原。
探索网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翻译】
老舍“并不太喜欢阅读译文”,可他对翻译,又别有见解。
在《谈翻译》里,他指出“搞创作的有遣字选词的自由,搞翻译的却没有;翻译工作者须随着原文走,不能望文生义,随便添减”,希望“最好是译者能够保持原著者的风格”,而且还说:“保持原著者的风格若做不到,起码译笔应有译者自己的风格,读起来有文学味道,使人欣喜。世界上有一些著名的译本,比原著还更美,是翻译中的创作。严格地说,这个办法也许已经不能叫作翻译,因为两种不同语言的创作是不会天衣无缝,恰好一致的。这种译法不能够一字不差地追随原文,而是把原文消化了之后,再进行创作。不过,这种译法的确能使译文美妙,独具风格。”
他这番大道理,于一般翻译而言,应无问题。但用于回译,似又不大讲得通——回译者,犹如一仆二主,需要“双重忠实”:要对原译者负责,还不能远离原著者。
如是而言,则只可寄望译文忠实,不能奢求“比原著还更美”。所以,翻译的第一稿,信、达而外,不必在乎“雅”,亦无需计较其他。假若期待“独具风格”,那就等修正时,用老舍的字汇,再图译文“神形具备”。
【修正】
从初译至定稿,前后修改四次。初稿的修订,重在保证译文准确,信实,通达顺畅;随后的修正,主要是用老舍的字汇和词汇,对字词进行替换,同时调整语句。
第一稿的修正,重在订正专有名词,别的原译改动,基本维持原样:“名不正言不顺”,人名和地名确定无误,还原方可免出差错。
人名及其称呼,看似简单,其实不然。以小妞子来说,还有两个昵称:瑞宣韵梅夫妇喊她“妞子”或“妞妞”;小顺儿和奶奶喊她,和小妞子自呼其名,都是“妞妞”,“妞子”不会挂在他们口头。但在英译里,Little Niu-Niu之外,只有一个Niu-Niu,究竟是“妞妞”,还是“妞子”一时很难把握。
又如李四爷的称呼,也因人而异,一变再变。“李老人”、“李老者”、“李四老人”、“李四大爷”,“四大爷”和“四爷”,交叉迭现,无一定规律。英译虽有Old Man Li、Fourth Master Li、Fourth Master和Fourth Uncle,却与中文并不完全对应。还原的时候,难免左支右绌:一个Fourth Uncle,到底是“四爷”,还是“四大爷”?
语境决定称呼,还原不可大而化之,因为在老舍心目中,称呼不是小事:
“我们应当与小说中的人物十分熟识,要说什么必与时机相合,怎样说必与人格相合。顶聪明的句子用在不适当的时节,或出于不相合的人物口中,便是作者自己说话。顶普通的句子用在合适的地方,便足以显露出人格来。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是最应注意的。”
(《言语与风格》)
探索网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地名及其关联词汇的还原,同样不能马虎。如第三十四章写北海公园,对白塔和荷花有如下描述:
The White Dagoba in the North Sea Park still stood proudly. The lotus in the lakes had still their red or white petals and gave out their pure fragrance. The altars, temples, and palaces, still shone majestically in their gold and green light.
直译即为:
“北海公园的白塔,仍然骄傲地立着。湖里的荷花依然开着红色或白色的花瓣,吐放着清香。祭坛,寺庙,还有宫殿,依然金碧辉煌,闪着光芒。”
从表面看,译文明白通畅,似无问题。可是,将之与此前描写什刹海的片段对看,比较一下“‘海’中的菱角,鸡头米,与荷花,已全只剩了一些残破的叶子,在水上漂着或立着”之句(《惶惑》之十九),就会马上意识到:lakes是“海”,不是“湖”,“湖里的荷花”得改成“海中的荷花”;“祭坛”和“寺庙”,也要改作“坛社”和“寺宇”,老舍用词如此,还原得随着他。
提及国家和民族,也可一看“the son of Han”之译。《饥荒》第二十一章之后,几次出现这个词组,以及相关的“the good son of Han”,似可译“汉族的儿子”和“汉族的好儿子”。但将之与上下文同读,感觉殊为异样,很不像老舍笔墨。反观本书前文,“汉奸”通篇可见,“中华民族”亦不稀罕,唯独不见“汉族”一词,足见老舍的民族观念,甚是近于梁启超之说,即“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遍俗称所谓汉族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他显然已弃用“汉族”之说。不过,将“汉族的儿子”改作“中华民族的儿子”或“中华之子”,又不大好用在老舍笔下。在直觉中,与其译“son”为“儿子”,不如译成“男儿”更为恰切;后者虽不见于本书,却在老舍其他的作品中相当多见。比如“跃进真如天马驰,乘风好女好男儿”是他题黄慎《孤崖清话图》的诗句,而在他一九三二年的《国葬》里,下列诗行更是赫然在目:
“‘爱国的男儿’用血写在一片木板上,
它将替你说:
你生在中华,为中华而亡。”
那么,不妨借来“男儿”一用,将之与“中华”相并,形成新的词组“中华男儿”,或“中华好男儿”。
这个“借词”的办法,即从作者其他的作品,借取“现成”之词,来补本书“不现成”之需,在回译中会经常用到。如《饥荒》第二十五章,写到白巡长感觉大事不妙,说“他很有可能因此给撤了差,一旦给撤差了,他自己就极有可能给饿死”,句中的“撤了差”和“撤差了”,即从《骆驼祥子》中借来:“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
说到字词的替换,有必要提一下语言的时代变化。一九五五年汉语规范化运动之后,老舍习用的词汇,不少遇到了新的情况:
(一)为他词替代,如“自傲”(“自豪”),“恨恶”(“憎恨”)和“助援”(“援助”);
(二)与他词并用,却比较少见,如“菜蔬”,“苦痛”和“带孝”;
(三)仍还通用,但部分意思已不复存在,比如“火炮”失去“爆竹”和“鞭炮”之意;与传宗接代相关的“香烟”,为“香火”取代。
也就是说,还原中不当心选错词,即会导致语言的“时代错乱”。这是一个不好回避的麻缠问题。本书前面写到瓜果菜蔬,涉及本名胡瓜的黄瓜,用词均为“王瓜”(一九三六年版《国语辞典》有“俗亦称黄瓜为王瓜”一说),如《惶惑》第十五章写祁家人见到常二爷,说“听他讲话,就好像吃腻了鸡鸭鱼肉,而嚼一条刚从架上摘下来的,尖端上还顶着黄花的王瓜,那么清鲜可喜”;但在《小说》月刊连载的《饥荒》前二十章里,“王瓜”全变成了“黄瓜”,如第九章就有“爬架的是黄瓜,那满身绿刺儿,头上顶着黄花的黄瓜”之句。难道是老舍笔误?不大可能。因为从一九三六年的《新韩穆烈德》(有句如“热洞子的王瓜,原先卖一块钱两条,现在满街吆喝一块钱八条”),到一九六三年在北京市第三次文代会上的发言《创作的繁荣与提高》(里面提到“北京的农业也丰富多彩,有旱地,也有水地,有在冬天还生产翠绿王瓜的菜圃,还有善产芍药、玫瑰的花农与出产蜜桃和小白梨的果园”),再到一九六五年的《正红旗下》(语及“到十冬腊月,她要买两条丰台暖洞子生产的碧绿的、尖上还带着一点黄花的王瓜,摆在关公面前”),从头到尾所用都是“王瓜”。有理由相信,《饥荒》前半部里出现的“黄瓜”,极可能系刊物编辑擅改。于是,还原之后的日本女人市场劫掠场面,就必须改回“王瓜”:“一个人抢了一棵白菜,就有另外一个人拿几条王瓜放到菜篮里”(第二十六章)。遗憾的是,一九九九年版《老舍全集》辑录残本《四世同堂》,依然沿袭旧讹,保留了“王瓜”和“黄瓜”并用的错误。
探索网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其实,“王瓜”一词之用,也是作者个性语言特色的展现,在成语、方言、俗谚,乃至虚字和标点的运用上,他有自己的讲究,因而他所用的句式,也会与他人有别。比如,关于成语和俗话,他说:
书本上的成语在适当的地方也可以用,但不能完全仗着他们美化语言。在叙述中,“适可而止”这句成语是可以用的,不必改用北京的俗语“该得就得”。可是,在写两个北京劳动人民讲话的时候,也许用“该得就得”更合适一些。何去何取,决定于生活。把“适可而止”放在一位教授嘴里,把“该得就得”放在一位三轮车工人的口中,也许是各得其所。这一雅一俗的两句成语并无什么高低之分,全看用在哪里。(《语言与生活》)
所以,通观本书不难注意,有些常见用语,如“含辛茹苦”、“千方百计”、“面面相觑”和“咬牙切齿”等,不会现于他的笔端;他用到的一些成语,也和通常所见有别,如“羞恼成怒”、“愁眉苦眼”(或“愁眉皱眼”)和“挨家按户”。
至于方言俗语,他的运用,似乎也非如一般所想,是“有闻必录”的,比如他不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将这个俗语加以改造,说成“睁一眼闭一眼”(《惶惑》第三十一章有“儿子们自有儿子们的思想与办法,老人们最好是睁一眼闭一眼的别太认真了”句)。但是,他究竟如何“改造”,因为没有证据,还原时极难把握。如第二十八章写金三爷心态变化,有这样一句:“小事情不要打扰我,仨芝麻俩枣的,我,金三爷,就不麻烦迈腿了。”这里的“仨芝麻俩枣”,会不会是“仨核桃俩枣”,或“仨瓜俩枣”之变呢?或许不是,或许根本就是原译笔误,怎么抉择煞费苦心。最后,鉴于后面两种用法,既不见于本书,也从他其他的作品里找不到,索性老实尊重原译,不加任何修正了。
一般来说,虚字的使用,似可稍微随便。老舍不然,他主张“……少用‘然而’、‘所以’、‘但是’,不要老用这些字转来转去”(《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在本书的虚字里面,“假若”、“假使”和“可是”最多,“如果”和“然而”几乎不见,也没有“但却”的用法,——他说过:“我不敢说像‘但却’之类的词汇是记者们发明的,可是不少记者的确爱用它,而许多中学生也跟着这么用。我希望《文汇报》的记者不再‘但’而且‘却’!”(《贺复刊》)。
他的语言运用,显然有一些界限,是不可逾越的。
同样,老舍用到语气词,尤其在对话当中,也不马虎。他说过,“语言要准确、生动、鲜明,即使像‘的’、‘了’、‘吗’、‘呢’,这些词的运用也不能忽视。”而在本书当中,为表示惊叹,感慨,或者疑问,用得很多的“呕”和“什吗”,几可视为老舍文风标志之一,但它们似乎已从现今人们的书面语里消失了,——还原的时候,要想法找回来,还得用妥当。
到了最后一次,亦即第四次译稿修订,则是对标点的调整。在原译稿中,老舍用得频繁的惊叹号很少见;他节制而用的破折号,却用得极为普遍。为了与原著保持“形似”,我参照老舍的写作习惯,尽量对部分标点,作了相应替换。
有人说翻译老舍,——不管是“复译”还是“回译”,犹如修缮古代文物建筑,要有修旧如旧的工夫,做到亦步亦趋,无过雷池一步;文字要尽量模仿老舍,甚至追随他擅长的北京方言俚语表达习惯。这是个过高的要求。照此而行,也容易使译者陷入另外一个误区,那就是“过度翻译”,让译稿中出现老舍不用,至少不会用在《四世同堂》中的土语,那就有过犹不及的嫌疑了。这也是我要尽力避免的。我更在意译文的忠实和准确,不会允许自己违背史识,擅自换“太阳旗”为“膏药旗”,改“青天白日旗”作“国旗”,以“中华民族万岁”代“中华民国万岁”。我知道,尽管注意到这些或表或里的问题,用字造句花足力气,也不一定保证自己的语言,能够化作完美的老舍笔墨。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
在定稿前夕,我又想起这样一段话:
“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四世同堂》版本,它既包括目前出版的最全的中文单行本的全文,即按老舍中文手稿排印的前八十七段,也包括由英文节译本转译回来的后十三段,全书共一百段,正好是老舍原来计划和实际完成的一百段。”
这是老舍的夫人胡絜青,为以哈考特版为底本所补译文字,所写下的肺腑之言。现在,目前的这个新译稿,使得老舍的原作,达到了一百〇三段。尽管它不是老舍原来计划和完成的手稿的全部,但我相信,也衷心祈望这个本子,能让新一代的读者,更进一步接近老舍原著。这勉强也可以说是对老舍蒙冤辞世五十周年的一点微薄纪念吧。
赵武平
探索网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